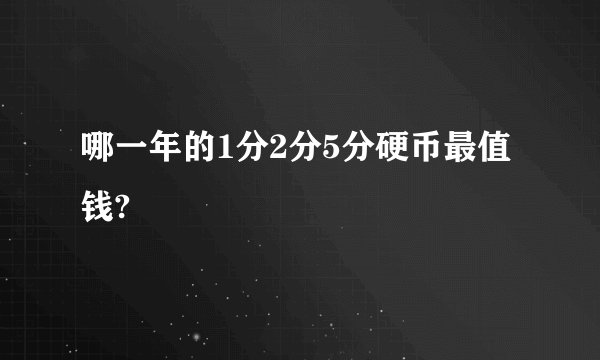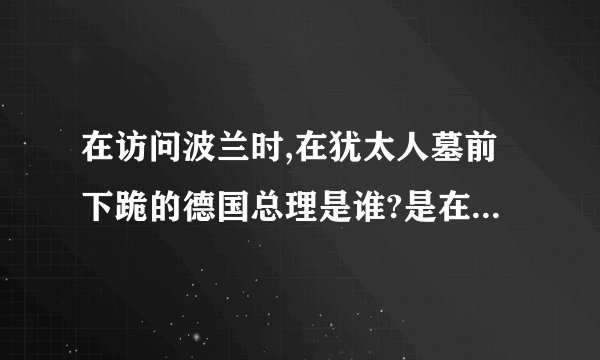
第一个向犹太人下跪赔罪的德国总理——勃兰特·维利访
作者:柏桦 编著
我下跪并不是因为我有罪……面对受害犹太人石碑,我不能仅仅面无表情地献上一个花圈就完事……应该有个举动。它对德国人和犹太人都有利,能为未来打通一条道路……
——勃兰特·维利
勃兰特·维利(1913—),西德政治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1969—1974)。1971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奥里亚娜·法拉奇(1930—),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活跃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外交界的一个“实话实问”的新闻人物,以多次成功地采访世界政坛的风云人物如基辛格、武元甲、西哈努克、勃兰特、英迪拉·甘地、巴列维、阿拉法特、邓小平等,被誉为“世界政坛采访之母”。
1973年8月28日和9月3日,奥莉亚娜·法拉奇分两次对勃兰特·维利进行了采访,主要针对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西欧及中东问题、德国与以色列关系以及勃兰特个人成长过程等。提问尖锐,回答巧妙,对话精彩。现选摘德国与欧洲话题的部分采访记录,以飨读者。
我的人生代价——从德国出走
奥里娅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勃兰特总理,坦率地说,我不知从哪儿开始提问。要问您的事情太多了,包括您的名字的来历。它不是您出生时的名字。您出生时叫赫伯特·弗拉姆……
勃兰特·维利(以下简称“勃”):是的,勃兰特·维利这个名字我是从1933年初开始使用的,貌锻是在我离开德国以前和纳粹分子上台以后。那是我用来从事反对希特勒的地下活动的“化名”。(对将赫伯特·弗拉姆改名为勃兰特·维利原因何在,勃兰特从没解释过有人说或许是对“烈焰”的联想而表达的一种革命意志。“勃兰特”一词德语意为火、烈焰—原书编者注。)我用这个名字在19岁那年逃亡国外,我用这个名字开始在报上发表文章,出版书籍。用这个名字,我从事政治活动,直到成年,直到战后又回到德国。我的一切都与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用我出生时的名字。
法:这就是说,您结婚和加入挪威国籍时也用勃兰特·维利这个名字。好吧,也许我们应该从这个问题谈起,也就是您曾多年成为另一个国家的公民。除犹太人外,当时离开希特勒德国的德国人并不很多。
勃:相反,离开的人不少。以我出生的吕贝克市为例,很多人都走了,几乎所有走的人年龄都比我大。
我为什么离开德国呢?要是我留下来,他们将逮捕我,并把我送进集中营。当时我没有多少逃脱的可能。即使不逃亡国外,我也必须离开吕贝克;但即使离开吕贝克,我也不能上大学。这是我出走的一个原因。
上完中学我干了一年的经纪人,这个工作还算有趣。但我想学历史,而当时在希特勒的德国学历史已不可能。因此只要我遇到合适的机会……当时我的小组里有一个人要逃往挪威。他准备在那里开设一个办事处,负责我们抵抗运动的事情。他一切都准备就绪,一个渔夫要从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地方把他接走。我的任务是帮他逃走。但是这个人没有走成。他被逮捕,送进了集中营。当时柏林的朋友们问我是否愿意代替他,我接受了。
我没想到这一走就意味着将在国外呆那么长的时间,因为很多人认为纳粹统治不会太久,有人认为它一年后就要完蛋,最多也不过4年。我虽不是乐观主义者,但是也认为不会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的时间更长,可是事实上却持续了12年。
法:正是您在斯堪的纳维亚度过的那12年,使您的对手们经常对您进行指责。因此,我的问题是:您对没有在德国直接参加对纳粹的斗争感到遗憾吗?
勃: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我的表现都说明:一旦需要,我随时准备冒生命危险。我曾秘密潜回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几个月后因为他们要逮捕我,我又第二次逃亡。我前往希特勒占领的挪威和瑞典。所以我也是冒过风险的。如果用推理的方法来考虑您的问题,那末我的回答是:
如果我不离开祖国而留在德国,也许我就没有同样的机会得到锻炼和成长,因而也不可能从事我在柏林时以及在那以后所从事的工作。我指的特别是我在欧洲和国际事务方面的活动。
自然,任何事情都必须付出代价。我所付的代价与我的大多数同胞所付的代价是很不相同的。我的代价就是出走。
是的,对有的人来说,这种支付代价的方式似乎会使他感到奇怪。所以这就成为我的对手们掀起反对我的运动的借口。
我对这些人的回答是:那么,许多德国人承认我、信任我也同样是奇怪的。我蔚的是奇怪,对吗?我应该说妙极了。许多德国人信任一个其生活经历与他们不同的人,这是一件很妙的事情。这个人的生活经历不比他们的好,但不同。
(1965年勃兰特经过斗争,终于成功而大权在握,这在德国简直是奇迹,因为德国人的禀性天生不赞成左派居多数。入主总理府是这位出生在吕贝克的流亡者的毅力和惊人抵抗力的胜利。尽管勃兰特的竞争对手阿登纳不惜攻击他有着“不明不白的出生”和“外来户”,但勃兰特成功了。
勃兰特用“一个其生活经历与他们不同的人”来巧妙回答其成功中为何得到德国人的信任,更使奥里娅娜·法拉奇感到他的机智与智慧。)
“挪威是我的第二祖国”
法:勃兰特总理,我猜测您在谈论出国后付出的代价时也暗指您失去德国国籍的问题。您在丢了德国国籍加入挪威国籍时有没有感到痛苦。
勃:没有。
法:为什么?您是不是太热爱挪威了?
勃:是的。我把挪威看成是我的第二祖国。如果一个人从小就去国外,在那个国家定居,生活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而且学会了那里的语言……我很快学会了挪威语,我并且学得不错。我曾多次说过,我用挪威文写的文章比用德文写的文章要好得多。
法:那末我想反过来问您,您在丢了挪威国籍又重新加入德国国籍时是否感到痛苦?
勃:没有。有的国家不要求你作这种选择。要是我成为美国公民,我就不需要归还护照,最多不过保持双重国籍。在挪威没有这种先例。要么是挪威公民,要么不是。因此我痛快地归还了挪威护照,而且我非常清楚,护照不会影响一个人的立场和原有的关系。我知道我还会回到挪威去,那里仍然有我的朋友,回去后,我仍然讲挪威话,总之,我原有的关系绝不会因为我缺乏一份护照而中断。许多人的护照不符合他们的国籍。要是您问我“难道护照不重要吗?”我的回答是:是重要的,特别是在通过国境时,但是证件的重要性经常是被夸大的。国民的身份是另外一回事。
不是祖国征服了我
法:很有意思。但是我不相信您回德国是出于偶然,而不是出于感情。
勃:然而事实却是如此,这不是一件涉及感情的事,不是。我回柏林只是因为柏林引起大家的兴趣,是东西方争执的中心,是个值得去的地方。
至于这一点加速了我确定自身归宿的进程,这是另一回事。我指的不仅是政治上归化的进程,而且也指与生活在苦难和失败中的人们融为一体。
当时的柏林是一片废墟,但在废墟中可以看到人民的优良素质。是的,这种素质往往在逆境中表现出来,每次都使人吃惊。啊,柏林人的士气从来没有像战后头几年那么高涨。即使在封锁时期,也没有那么高涨,因此,我确定自身归宿的进程……
法:但是您说的归宿是指的什么?是大家称作回祖国的概念吗?
勃:不是,不是祖国征服了我,而是人民,是经历了专制、战争和崩溃之后又试图在自由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生活的人民。
是的,是人民使我重新成为德国公民,是他们每个人那种惊人的工作热情,是他们那种完成任何工作的能力,是他们那种互相帮助的精神……我们变得富裕之后便失掉了这种精神。
当时的经济是困难的,但气氛给人以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印象。
您明白吗?这与其说是民族主义的因素,还不如说是人的道德价值的问题。我愈想愈深信,关于欧洲的思想,更确切地说关于欧洲的思想,在我身上扎根,正是我在柏林的那些岁月里。
“我在承担作为一个德国人的责任时,也努力成为一个出色的欧洲人”
勃:啊……让一个年近六旬的德国总理承认这一点未免太过分了,特别是他知道欧洲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发展。也不能要求我这样行动,甚至也不能要求我给人这样的印象。
可以这样说:我在承担作为一个德国人的责任时,也努力成为一个出色的欧洲人。至于您的问题,我只能回答:我不是欧洲人,我是德国人。
要把已掌握了政权的罪犯赶下台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采访勃兰特之前,奥里娅娜·法拉奇曾仔细地研究过他的性格,印象格外深刻:
勃兰特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年轻政治家,他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充满活力,他有着稳重而朴实无华的气质。新闻界和政界都经常用“超凡魅力”的话来形容他。
勃兰特待人接物充满人情味,性格坚强,虽不如总理阿登纳那样德高望重,颇具权威,但他喜欢依靠说服、呼吁理智和道德勇气以及依靠政治行动的说服力来赢得民众对他自然而然的信任。
在政治上,勃兰特推行“和平政策”努力去实现使“另一个德国”出现在世界上的目标,其中寻求同自己本身以及从前的敌人取得谅解。勃兰特作为德国总理跪倒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纪念碑前的举动轰动了世界,他的所作所为,赢得了世界的普遍赞誉。
新闻媒体评价说:“敢于这样做的,也许只有这位能被西方和东方的抵抗运动见证人都视为自己人的德国总理。”
与此同时,他对战争中德国人的罪过与责任论述更加理智负责任。)
想到这里,奥里娅娜·法拉奇说:我明白了。那末……我想到了您对华沙犹太人聚居区的访问。
1913
勃兰特·维利